尊儒教為國教并以孔子紀年
——戊戌亡命后康有為的儒教思惟
作者:唐文明
來源:作者授權儒家網發表
選自作者所著《敷教在寬:康有為儒教思惟申論》,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2012年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閏七月初二壬午
耶穌2017年8月2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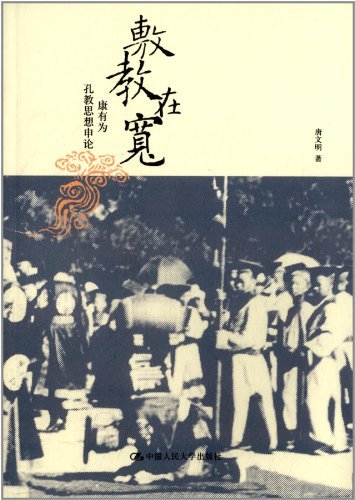
1911年在japan(日本)出書的《戊戌奏稿》中載有《請尊儒教為國教,立教部教會,以孔子紀年而廢淫祀折》(以下簡稱“國教折”)。由于在《杰士上書匯錄》中發現了後面討論過的保教折,所以論者提出,國教折是康有為后來根據原來所上的保教折“改刪而來”。[1]
比較一下保教折和國教折,發現無論從立意到內容,二者的差異都很是之年夜,是以,說國教折是根據保教折改刪而來其實長短常勉強的。不過,從《我史》的有關文字可以證實,國教折與保教折的確具有對應關系,即就康有為的寫作動機而言,國教折的確是對保教折的重撰。
《我史》“光緒二十四年”條下記載說:“于初一日……又陳請廢陳腔濫調及開儒教會,以衍圣公為會長,聽全國人進會,令上帝、耶穌教各立會長與議定教律。凡有教案,歸教會中依照議定之教律商辦,國家不與聞。并進呈《孔子改制考》,請聽沿邊港口準用孔子紀年。”[2]
茅海建指出,《我史》手底稿中“并進呈《孔子改制考》,請聽沿邊港口準用孔子紀年”之語為后來添加,補外行間與頁腳。[3包養網VIP]以孔子紀年是國教折的一個要點,而在保教折衷最基礎沒有出現。既然康有為在此增添了以孔子紀年的說法,就表現他將專門論及以孔子紀年的國教折系之于光緒二十四年蒲月一日進呈的論及儒教的折子,即后來在《杰士上書匯錄》中發現的保教折。
還須指出的是,在國教折衷,并沒有“請聽沿邊港口”等字眼。由此我們可以推斷,《我史》中“并進呈《孔子改制考》,請聽沿邊港口準用孔子紀年”之語的添加要早于國教折的撰寫,因為假如國教折的撰寫在先,那么,康有為在修正《我史》時增添國教折衷沒有的“請聽沿邊港口”等文字就是難以懂得的。
還有一個證據可以說明這一點。國教折衷提到此次進呈的與儒教有關的書目除了《孔子改制考》的刻本之外,還有《新學偽經考》和《董子年齡學》。孔祥吉指出,《孔子改制考》并非以刻本進呈,而是康有為從頭繕寫后進呈的,且《新學偽經考》和《董子年齡學》二書康有為并未進呈。[4]康有為之所以掩蓋本身以繕寫本而非刻本進呈的事實,是有明確的緣由和意圖的。[5]
可以想見,康有為在國教折衷將進呈的書目從《孔子改制考》擴年夜到《新學偽經考》和《董子年齡學》,同樣并非隨意為之。假如國教折的撰寫在先,那么,康有為在修正《我史》時所增添的字樣就不會僅僅是“進呈《孔子改制考》”了,而應當是“進呈《孔子改制考》、《新學偽經考》、《董子年齡學》”了。
那么,國教折畢竟撰于何時呢?雖然今朝對這個問題我們無法獲得一個確鑿的謎底,可是,將國教折與康有為其他著作中的有關內容作一對照性的剖析,我們大要可以得出一個比較清楚的結論。
如前所述,在保教折衷,康有為一開始就提出教案問題,然后順著若何解決教案問題的思緒引出本身的儒教建制主張。在國教折衷,康有為一開始則是提出淫祀問題,然后順此引出本身的儒教建制主張。
對于淫祠遍布中國的迫害,康有為言之鑿鑿:“夫神道設教,圣人所許,鄉曲必廟,禱賽是資。而牛鬼蛇神,日竊噴鼻火,山精木魅,謬設廟祠,于人心無所激厲,于俗尚無所風導,徒令妖巫欺惑,神怪驚人,虛糜牲醴之資,日竭噴鼻燭之費。而歐美游者,視為野蠻,拍像傳觀,以為笑柄,等中國于爪哇、印度、非洲之蠻俗罷了。于國為年夜恥,于平易近無少益。”[6]
接著,康有為剖析了淫祠遍布中國的緣由。
在康有為看來,從宗教進化的角度上看,儒教無疑是最先進的,孔包養一個月子乃是文明世之教主:
“夫年夜地教主,未有不托神道以令人尊信者,時地為之,若不假神道而能為教主者,惟有孔子,真文明世之教主,年夜地所無也。”[7]
宗教進化的思惟,康有為獲之甚早。在出書于1898年春的《japan(日本)書目志》中,康有為在“宗教門”下所加的按語就是以宗教進化為主題,此中他以勇、仁、智說宗教進化之跡,并在闡明“教必明之鬼神”的基礎上指出人類聰明越發展,就越是重視精力,即他所謂“人智愈鑿,賤形而尊魂”:
“合無量數圓首方足之平易近,必有聰明首出者作師以教之。崇山洪波,梯航未通,則九年夜洲各有開天之圣以為教主。泰初之圣,則以勇為教主;中古之圣,則以仁為教主;后古之圣,則以知為教主。同是圓顱方趾則不畏敬,不畏敬而無以聳其身,則不遵信,故教必明之鬼神。故有群鬼之教,有多神之教,有合鬼神之教,有一神之教。有托之木石禽畜以為鬼神,有托之尸像以為鬼神,有托之空虛以為鬼神,此亦鬼神之三統、三世也。有專講體魄之教,有專講魂之教,有兼言形魂之教,此又教旨之三統也。老氏倡不神之說,阮瞻為無鬼之論,宋賢誤釋為二氣良能,而孔子六經、六緯之言鬼神者晦,而孔子之道微。豈知精氣為物,游魂為變,《詩緯》以魂為物本,魂靈固孔子之道。而年夜地諸教乃獨專之,此亦宋賢不窮理而誤割地哉!人智愈鑿,賤形而尊魂。必矣,后十年魂教其年夜明乎!日人所譯佛、婆羅門、耶、回之書,及《宗教進化論》、《宗教新論》、《未來世界論》、《六合镕造化育論》,環偉連忭而俶詭可觀也。japan(日本)神學乃儒、佛未東渡之前為東夷舊俗,無足觀焉。”[8]
從這一段按語以及按語後面所列的書目可以斷言,其時康有為對東方宗教學界關于巫術與宗教的區分、多神教與一神教的區分、天然宗教與啟示宗教的區分、甚至啟蒙運動以來的感性宗教等概念都有所清楚,並且他將宗教進化與他的三世說也關聯起來了。
能夠看到的是,關聯于三世說的宗教進化思惟,恰是國教折的一個焦點思惟。回到淫祠何故遍布中國這個問題,既然儒教是最先進的宗教,而儒教從漢代以來就一向是中國的國教,那么,中國就不應該出現淫祠遍布的情況。
對此,康有為提出他對中國風俗之懂得的另一面來加以解釋:“竊惟孔子之圣,光并日月;孔子之經,流亙江河,豈待臣愚有所贊發!惟中國尚為多神之俗,未知專奉教主,以發德心。”[9]
聯系康有為的宗教進化思惟,這里的意思當然是說,從中國的風俗來看,還需求從愛崇多神之狀況進化到專尊一教。言下之意便是,儒教雖然從漢代以來就是中國的包養意思國教,但儒教并沒有真正澤被百姓。[10]
康有為還以歐美為例,來說明在神道教中一神教的先進性:“旋觀歐美之平易近,祈禱必于天神,廟祀只于教主,七日齋潔,跪拜誦其教經,稱于神名,起立恭默,雅琴合歌,一唱三嘆,警其天良,起其齊肅。此真得神教之意,而又不掉尊重之心。”[11]
在此值得留意的是,除了國教折,康有為明確論述神道為教與人性為教之間的區別以及孔子為文明世之教主,是在寫作于1904年的《意年夜利游記》中。其論神道設教之法云:
“夫教之為道多矣,有以神道為教者,有以人性為教者,有合人、神為教者。要教之為義,皆在使人往惡為善罷了,但其用法分歧。圣者皆是醫王,并明權實而雙用之。古者平易近愚,陰冥之中事事物物皆以為鬼神,圣者因其所明而怵之,則有所畏而不為惡,有所慕而易向善。故泰初之教,必多明鬼;而佛、耶、回乃因舊說,為地獄、地獄以誘平易近。今讀佛典言地獄者,尚為之震栗。而凡人循行城隍、廟廊之地獄,亦多有所動而改過者。歐亞之人,俗皆略同,此耶、回所以成教宗而能年夜行。在中世愚俗,其無益于人心風俗,豈淺鮮也!管子曰:‘不明鬼神,則陋平易近不悟。’孔子亦言:‘圣人以神道設教,百眾以畏,萬平易近以服。’今六經言鬼神者甚多,肅祭奠者尤嚴,或托天以明賞罰,甚者于古來日、月、食、社、稷五祀亦不廢之,此神道設教之法也。”[12]
其論孔子以合人、神為教而以人性為重云:
“孔子惡神權之太昌而年夜掃除之,故于當時一切神鬼皆罷棄,惟留天、地、山水、社稷五祀數者,以臨鑒斯平易近。雖不專發一神教,而掃蕩舊俗這般,功力亦極年夜矣!其仍留山水、社稷五祀者,俾諸侯、年夜夫、小平易近切近而有所畏,亦不得已之事也。若至人智年夜明,則泛掃之亦易事耳。孔子以掃蕩舊時神俗,故罕語神,又曰‘敬鬼神而遠之。’若其尊天之丁寧直捷,以《詩》、《書》考之,幾于語必稱天。如《詩》之‘明明在上,赫赫鄙人,天難忱斯,不易為王,天位殷適’,五語四稱天。又曰:‘天主臨汝,無貳爾心。’此雖耶、回之一神教,亦豈能過?況孔子實為改制之教主,立三統三世之法,包括神人,一切莫不覆幬,至今莫能外之。其三世之法,與時變通,再過千年,未能出其范圍。朱子不深明本末,乃僅發明《論語》,以為孔子之道在是,則割地偏安多矣。此乃朱子之孔子,非真孔子也。或乃不知孔子實為孔教之祖,誤以為哲學之一家,乃以梭格拉底比之,則亦朱子之孔子罷了。但孔子敷教在寬,不尚科學,故聽包養行情人不受拘束,壓制起碼。此乃孔子大公處,而教之弱亦因之。然治古平易近用神道,漸進則用人性,乃文明之進者。故孔子之為教主,已加進一層矣。治較智之平易近,教主自不克不及太尊矣。”[13]
兩相對照之下可以發現,國教折衷關于神道設教與孔子為文明世之教主的思惟與《意年夜利游記》中對以神道為教與以人性為教的論述長短常接近的。並且,國教折衷還提到“近人遂妄稱孔子為哲學、政治、教導家,……遂令中國誕育年夜教主而掉之”,此與《意年夜利游記》中批評以孔子為蘇格拉底式的哲學家略同。
此外,在同樣寫作于1904年的《英國監布列住年夜學華文總教習齋路士會見記》中,康有為同樣闡述了以神道為教與以人性為教的區別及二者各自的意義,也同樣批評了“謂孔子乃哲學家、政治家、教導家而非教主者”的觀點,可以說與《意年夜利游記》和國教折衷的有關論述基礎分歧。[14]而我們了解,以孔子為哲學家、政治家、教導家的觀點背后是認為儒教不是宗教,而儒教能否是宗教在戊戌時尚未成為士夫爭論的議題。[15]
再次回到淫祠何故遍布中國這個問題。既然孔子為文明世之教主,而中國之俗仍尚多神,那么,康有為就提出,淫祠遍布中國的最基礎緣由,在于朝廷未能令全國國民專祀孔子:
“中國數千年來,敬教正學,凡歷代儒先所論,我朝圣訓所垂,罔不迪于正典,力辟怪邪。而坐聽妖巫神怪不經之事,年夜供奉于平易近間,積久愛崇,或光列于祀典,豈不異哉?歷朝間有剛正之年夜臣,時請為淫祀之嚴禁,明主在上,亦或采行,乃不旋踵而淫祀復興,遍于平易近間。推原其故,蓋朝廷雖言敬教正學,只等具文,而未令全國國民專祀先圣故也。”[16]
同時,康有為還提到,在明代其實已經有了平易近間祭奠孔子的先例,只不過在清代又被制止了:“聞昔在明世,平易近間另有祠祀孔子者。至康熙時,御史吳培乃始奏禁婦女進孔廟燒噴鼻。自是禁平易近間廟祀孔子,以為愛崇先圣,豈知圣教從此不及于平易近矣。圣教日微,而淫祀日盛。”[17]
順著若何解決淫祠問題這個思緒,康有為起首提出“何不直祀孔子,同奉教主”的主張,然后進一個步驟闡發了人人皆可祀天之義。他廣引經典,以“常人皆天之子”立論,提出為順應升平之世,朝廷應當“正定其禮”以令國民祀天:
“臣竊謂中國祀法,有過尊之弊,而年夜害生焉。《谷梁傳》述孔子之包養甜心網年夜義,曰‘人非天不生,非父不生,非母不生,故謂天之子也可,謂之母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故王者稱為皇帝,不過取尊稱云爾,實則常人皆天之子也。《易》曰:‘六合氤氳,萬物化醇。’董仲舒述孔子年夜義亦曰:‘天者,人之祖父也。’人既不忘所生,祀其祖、父,又豈可忘所自出而不祀天哉?王者至尊,為天之子,宜祀天;國民雖卑,亦天之子也,亦宜祀天也。不過古者尊卑過分,故殊祀典,以為禮秩,豈所論于今升平之世哉?《論語》:‘子路請禱于天。’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洗澡,可以祀天主。’然則孔、孟年夜義,許人人禱祀天帝矣。且今功令即不定國民祀天,而平易近間歲時向空,無不祀天者。既久甜心寶貝包養網聽之而不由,何不因此正定其禮乎?即今欲禁之,則基督之教人,皆日跪拜天主矣。信教不受拘束,為憲法年夜義,萬無禁理。若實與而文不與,于平易近教既年夜損,于國秩又何益哉?”[18]
在闡述了國民祀孔、國民祀天之義后,康有為提出了祀天以孔子配的軌制建議。這項建議不見于康有為辛亥以前的其他著作,辛亥以后則有一篇文章專門討論這個問題,即1913年發表于《不忍》雜志的《以儒教為國教配天議》。就是說,假設我們能夠證明國教折寫于辛亥以前的話,那么,這意味著康有為第一次提出祀天以孔子配的軌制建議恰是在國教折衷。[19]
從相關實踐來看,我們現在能夠了解的,是陳煥章在1899年就在本身家祠中祀天以孔子配了:
“吾昔在高要創昌教會,即設圣位于硯洲鄉之陳氏祠,繼又設圣位于紐約之中華公所,后又設圣位于硯洲書院,往歲冬至且在硯洲南郊高筑天壇,以祀天而推圣師為主,以實行公羊無主不止,及中廳配天之義。今春在鄉建勵剛家塾,以祀先君麗江公并及三代,則又特奉昊天天主與至圣先師之牌位而崇祀之,以創尊天尊圣尊祖之儀,而為三本一堂之制。皆此志也。今國人莫不有家,家莫不祀其祖先,蓋報本之教然也。曷不推年夜報本之義,而宗祀孔子于家,以配天主,且以時讀經,以為安居樂業之計乎。誠如是,則家家皆有一儒教堂,處處皆有無數孔宅矣。”[20]
三本堂也見于康有為暮年在上海設立的天游學院。劉海粟回憶說:“學院右邊有一間平房,門上康師長教師題著‘三本堂’橫匾。我請他解釋,他說:‘人受生于天,受教于圣,傳類于祖若怙恃,三者人生之本,絕不成忘,每逢朔看,必率兒孫后輩至三本堂焚噴鼻叩頭。孔子圣誕,一切學子皆來拈噴鼻。’”[21]
假如陳煥章在家祠中祀台灣包養網天以孔子配的做法來自康有為的話,那么,我們說,康有為至多在1899年之前就有了這個設包養違法法,但從康有為的現存文獻來看,他對祀天以孔子配這一軌制設計的具體闡述則初見于國教折。我們了解,梁啟超曾稱康有為為“儒教之馬丁·路德”,據說是出于康有為的自況,這個說法當然重要并不是說康有為以基督新教為藍本——或模擬基督新教——而樹立儒教,而是說,康有為對于儒教的改造,類似于馬丁·路德對于上帝教的改造。[22]
比較一下我們會發現,康有為的儒教改造與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造最類似的即在人人可以祀孔、人人可以祀天這一點上。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造是通過“因信稱義”的教義而使信徒能夠直接與天主溝通,在客觀上減弱了教會的權力;康有為的儒教改造則通過徵引經典而提出人人可以祀孔、人人可以祀天的主張,關聯于當時的實際狀況,這一主張當然意味著打破底本由官方壟斷的祀天、祀孔權力。
我們了解,根據文獻記載,上古時期的中國曾發生過一次宗教改造,史家刻畫為從“家為巫史”到“絕地天通”,假如不考慮此中“巫史”概念與后來孔教義理之間的實質差異的話,那么,我們說康有為的儒教改造所遵守的路線其實是類似于從“絕地天通”前往到“家為巫史”。
另值得留意的,是在國教折衷,康有為依據他的三世說,刻畫了中國政教關系應該遵守的發展途徑,即從適應于據亂世的治教合一發展到適應于升平世的治教分途,他也明確指出,在這一發展過程中,要點是從原來的“立全國義、立宗族義”發展到今后的“立國平易近義”:
“夫孔子之道,廣博廣泛,兼該人神,包羅治教,固為至矣。然因立君臣夫婦之義,則婚宦無殊;通飲食衣服之常,則齊平易近無異。是以之故,治教合一。奉其教者,不為僧道,只為國民。在昔一統閉關之世也,立義甚高,厲行甚嚴,固至美也。若在當代,列國縱橫,古今異宜,亦少有不用盡行者。其條頗多,舉其年夜者,蓋孔子立全國義,立宗族義,而今則純為國平易近義;此則禮規不克不及無少異,所謂時也。孔子自有平世之義,臣所輯《年齡筆削年夜義微言考》,略發明之。但今未明,若盡以據亂舊道繩人,則時義事勢不克不及行;若不以孔子年夜教為尊,則人心世道不成問。故今莫若治教分途,則實政無礙而人心有補焉。”[23]
我們了解,康有為原來認為中國兩千年總總皆小康之道,而東方已先中國一個步驟漸至年夜同。但他后來轉變了見解,認為東方與中國差未幾皆處于據亂之世,而尚未達至升平之世。他的這一見解的轉變,恰是在1904年游歷歐洲之時。[24]
此義見于《意年夜利游記》:“竊觀今者歐美風俗人心,與中國正相若,其往性善不受拘束,皆甚遠也。國爭若是,險詐橫生,此正年夜行《年齡》之時,且一切據亂之義,尚合于今時,而萬不克不及求之高遠。吾昔者視歐美過高,以為可漸至年夜同,由今按之,則升平尚未至也。孔子于本日,猶為年夜醫王,無有能易之者。”[25]
可見,國教折“包養ptt立國平易近義”背后對包養犯法嗎時代性質的判斷與《意年夜利游記》中對時代性質的判斷是分歧的,即二者皆斷當下的時代為據亂世,而所提治教主張皆留心于若何從據亂世達至升平世。
隨后,康有為提出了“官立教部,而處所立教會”的國教主張,并明確闡述了“政教各立,雙輪并馳”的強國衛教之策:
“夫舉中國人皆儒教也,將欲令治教分途,莫若專職以守舊之,令官立教部,而處所立教會焉。首宜定制,令舉國罷棄淫祀,自京師城野省府縣鄉,皆獨立孔子廟,以孔子配天,聽國民男女皆祠謁之,釋菜奉花,必默誦圣經。地點鄉市,皆立孔子教會,公舉士人通六經、四書者為講生,以七日歇息,宣講圣經,男女皆聽。講生兼為奉祀生,掌圣廟之祭奠灑掃。鄉千百人必一廟,每廟平生,多者聽之。一司數十鄉,公舉講師若干,自講生選焉。一縣公舉年夜講師若干,由講師選焉,以經明行修者充之,并掌其縣司之祀,以教人士。或領學校,教經學之席,一府一省,遞公舉而益高尊,府位曰宗師,省曰大批師,其教學校之經學亦同。此則于明經之外,為通才博學者矣。合各省大批師公舉祭酒老師,耆碩明德,為全國教會之長,朝命即以為教部尚書,或謂年夜長可也。各國學校,皆隸于教,學誕辰必頂禮,況我孔子,向專為學校所奉哉?應密其儀節矣包養意思。至凡為傳教奉職講業之人,學業言行,悉以后漢、宋、明之儒先為法。矩矱禮法,不得少逾,執持年夜義,匡弼時風。雖或極迂,非政客士流所堪,難從難受,而廉恥節義,有所扶賴。政教各立,雙輪并弛,既并行而不悖,亦相反而相成。國勢可張,圣教日盛,其于敬教勸學,匡謬正俗,豈少補哉?”[26]
從下面的引文可以看到,能夠讓良多人深感不測且難以想象的是,康有為在此提出立儒教為國教的主張,恰是為了在軌制設定上實現政教分離。
在康有為看來,就中國而言儒教與君主制在漢代以來的結合可謂至美,但那種治教合一的形式僅僅適應于往昔一統閉關之世,而現在的世界則是列國縱橫,所以,政治軌制要發生變化,儒教的落實方法也要發生變化。正如政治軌制的變化重要是以“國平易近義”為圭臬一樣,儒教的落實方法的變化也必須以“國平易近義”為圭臬。
既然從漢代以來儒教一向是中國國平易近的主導性教化,那么,以“國平易近義”為圭臬來考慮儒教的落實方法天然就是在新的政治軌制架構內立儒教為國教,而這個從頭安頓儒教的步驟也就是治教分途,即分別樹立儒教軌制與政治軌制。[27]
為了實現政教分離而主張立儒教為國教,毫無疑問這是國教折的焦點思惟。此中,一個以“國平易近義”為圭臬的現代國家構想呼之欲出。需求指出的是,康有為曾在兩種分歧的意義上應用“國教”這個概念,其一是一個指向軌制設定的、具有規范意義的概念,其二是一個指向客觀事實的描寫性概念,即用來描寫他所認為的漢代以來儒教就成了中國的國教這一事實。更多的時候,康有為是在第二種意義上應用“國教”概念的。
以國教折為例,標題中“請尊孔圣為國教”的提法似乎意味著這里的“國教”概念基礎上是一個指向軌制設定的、具有規范意義的概念。國教折的註釋中只要兩處出現“國教”一詞,分別是開始時的“以重國教”和結尾處的“以崇國教”,二者的提法基礎雷同,意味著註釋里的“國教”概念基礎上是一個指向客觀事實的描寫性概念。
在寫作于1904年的《英國監布列住年夜學華文總教習齋路士會見記》中,康有為說:“中國數千年風俗之宜、好事之盛,無有如孔子者,此為吾國國教也。”[28]這是在第二種意義上應用“國教”概念;在統一段,康有為又有“宜立孔教為國教”的說法,這是在第一種意義上應用“國教”概念。是以,說康有為主張立儒教為國教,更確切的意思是說他主張將漢代以來一向是中國國教的儒教予以政治上的從頭確認和軌制上的明確安頓。[29]
在下面的這段引文中有一個問題值得留心。此中康有為談到縣、府、省等各級的講師或宗師“或包養意思領學校,教經學之席”,還引其他國家學校的情況加以比較、說明:“各國學校,皆隸于教,學誕辰必頂禮,況我孔子,向專為學校所奉哉?應密其儀節矣。”在國教折的最后,康有為還提出了改淫祠為孔廟或學校的建議。
我們了解,在保教折衷,并沒有提到學校,在針對淫祠問題而提出的建議中也只是說改淫祠為孔廟。學校之開設,始于光緒帝1898年7月3日的圣諭。隨后康有為上了一道折,即後面討論過的《請改直省書院為中學堂鄉邑淫祠為小學堂令小平易近六歲皆進學折》,建議開設中小學及高級學堂,此中不再建議改淫祠為孔廟,而是建議改淫祠為小學。國教折最后建議改淫祠為孔廟或學校的建議顯然是康有為后來關聯于光緒帝開學校之圣諭而有興趣補寫的。
至于“各國學校,皆隸于教,學誕辰必頂禮”的情況,在康有為戊戌以后的著作中則見于1904年他游歷英美年夜學所寫的游記。如在《英國監布列住年夜學華文總教習齋路士會見記》中,康有為在述及劍橋年夜學的教堂時說:“其祈拜耶穌之殿,尖塔無數,聳峭宏麗。蓋每校有之,而總年夜學別為一所焉。蓋凡教學,必尊其先圣先師,其中西之通義也。遍觀各國年夜中小校,莫不皆同。其本校傳授之著名者,懸其像于中,所以敬先師也。皆有祈拜耶穌之殿,所以敬先圣也。吾國人之就學者,雖非同教,包養一個月既進其學,亦施敬焉。其重先圣先師亦至矣!”[30]
在同樣寫作于1904年的《蘇格蘭噫巴顛年夜學參觀記》中,有如下的記載:“有祭殿,甚莊嚴,以祈于先圣耶蘇者也。每來復日,教習率學生習焉。蓋歐土學校,無不有殿以尊先圣者。一室遍懸前教習像,數百年中之名師皆備此,則尊先師也。立學必尊先圣先師,以教后士,此真中西所同。我國之立學,宜尊孔子,乃義之宜。”[31]
在以治教分途為宗旨提出了“官立教部,而處所立教會”的國教建議之后,康有為接著提出了以孔子紀元的建議:
“抑臣更有請者,年夜地各國,皆以教主紀年。一以省人記憶之力,便于考據;一以起人崇奉之心,易于尊行。japan(日本)無教主,亦以開國二千五百年紀元,與其時王明治年號并行。一以歸當王,一以便考古。若吾國歷朝數十,閱帝數百,年號幾千,記述既艱,考據未便,茍非通博專門,古人不知何世。既為前代,無關尊王,不若以教主紀年,更于敬教有補。”[32]
從現有文獻看,康有為最早討論紀元問題是在《實理公法全書》的“紀元紀年用歷”條下。在公法部門,他主張以地球開辟之日紀元,其言曰:“以地球開辟之日紀元,合地球諸博學之士者,考明古籍所載最可托征之時用之。而遞紀其以后之年歷學,則隨時取歷學家最精之法用之。”在比例部門,康有為則分別批評了以圣紀元、以君紀元和以事紀元的“無益于人性”。其批評“以圣紀元而遞紀其以后之年,倒紀其以前之年”曰:“此法甚包養dcard分歧實理。蓋圣人以前之人,不克不及知有后來之圣,倒紀其年,則無理矣。倘同時而數圣之功相若,則將各有紀元紀年,甚無益于人性矣。后人知識固甚于後人,其功亦可過後人。然則不令后人有改元之事,固與正義分歧;或令其可以改元,則數數改元,亦無益于人性也。”隨后康有為則很是簡略地批評以君紀元與以圣紀元比擬“更無益人性”,而以事紀元則尤為陋習。[33]
康有為在《實理公法全書》中提出的以地球開辟之日紀元以及與此相關的對以圣紀元、以君紀元和以事紀元的批評可以與《年夜同書》中的年夜同紀元思惟相對照。
在《年夜同書》中,康有為基于他的三世說刻畫了人類社會在紀元問題上的進化軌跡。
起首,他指出歷史上的紀元“或以君主,或以教主,或以立國,年夜率始于小君主,中于年夜帝主,而終于年夜教主也。”[34]接著,他論及在歷史進化過程中以教主紀元何故會代替以君主紀元,并順帶指出中國宜以孔子紀元:
“常人服從君主之權勢,不如服從教主之品德。以教主紀年,于義最年夜,于力最省,允為宜也。若中國既非耶教,自宜以孔子紀年。……從后百年,君主當不現于年夜地上,君主紀元之義,不俟年夜同世而先絕矣。非文明年夜國,亦必不克不及久存至于年夜同之世,然則建國紀初祖之義亦必不克不及存矣。然則所存者,惟教主紀元一義耳。”[35]
然后,康有為提出,以教主紀元與年夜同之世不相洽,年夜同之世當以年夜同紀元:
“然諸教競爭,各尊其包養網心得教,誰肯俯就?此事人人各有自立之權,不受拘束之理,不克不及以多數勝少數論也。若本日耶元之理,至年夜至盛矣,然十九世、二十世紀等字,終非孔、佛、婆、回之教之人所甘愿。且新理日出,舊教日滅,諸教主既難統一全地,終當有見廢之一日。此年夜劫難挽,亦與國主略同,但少有久暫鉅細之殊耳。然則君師、國祖之紀元并廢,年夜同之世宜以何者紀年乎?欲為年夜同之世紀年,即以年夜同紀年為最可也。地既同矣,種既同矣,政治、風俗、禮教、法令、懷抱、權衡、語言、文字無一分歧,然則不以年夜同紀年而以何哉!吾敢斷言之曰:來者萬年,必以年夜同紀年,雖萬國之文字有殊,而義必不克不及外之也。”[36]
之后又有當今之世宜以教主、年夜同紀元并行之說:
“今歐洲雖久以教主紀年,而又未嘗不間紀君主之年者,如japan(日本)稱立國幾年而又稱其君主紀年。蓋紀事各有宜,無妨鉅細兩元并記之,計久遠者從其年夜元,紀近事者聊從小元,現在中國人亦多有以孔子與君紀元并稱者矣。既因現時淺顯之宜便,又順將來年夜勢所必趨,莫若于今兩元并紀焉。”[37]
最后,康有為聯系萬國聯盟之近事,發揮庚子更始之義,提包養妹出應以1901年為年夜同元年:
“近年以年夜同紀元,當以何年托始乎?凡事必有所因,端必有所指,年夜同因之所托,必于其年夜地年夜合之事起之。近年年夜地萬國年夜合之年夜事,其莫如俄皇所倡在荷蘭之萬國聯盟矣。是事也,起于己亥,終于庚子。庚者,更也;子者,始也。庚子之冬至為西歷一千九百零一年,耶紀以為二十世開幕之一年者。當即以庚子春分為年夜同元年托始之正初一日。”[38]
在《實理公法全書》中,康有為提出以地球開辟之日紀元,是因為他信任通過考明古籍可以確定地球開辟于何時;在《年夜同書》中,康有為則認為地球開辟于何時無法確定:“年夜地之生,不知其始,或謂數萬年,或謂數百萬年,皆推測之說,非必實也。”[39]這實際上意味著他否認了以地球開辟之日紀元的能夠性。
在《實理公法全書》中,以圣紀元和以君紀元皆在康有為的批評之列;在《年夜同書》中,康有為則基于他的三世說確定了以圣紀元和以君紀元的歷史公道性,同時也提出這兩種紀元將隨著歷史的不斷進化而滅亡。兩相對照之下,盡管康有為在前后兩個文本中對以圣紀元的評價在傾向上有明顯的分歧,但有一點是明白的,即他主張在尚未進至年夜同紀元之前,中國宜以孔子紀元。
康有為不僅在理論上闡述以孔子紀元的公道性,還英勇地將之付諸實踐。之所以說他英勇,是因為在當時的環境里以孔子紀元是一件很犯諱的工作,既有能夠被認為是對正統歷法的挑戰,更有能夠被認為是對當時的清朝天子甚至整個年夜清王朝的不恭。
1896年1月12日由上海強學會發行的《強學報》就是以孔子紀元的,而根據《我史》的記述,以孔子紀元在當時惹起了強烈震動,而強學會的被封,亦與以孔子紀元有關:“吾以十仲春母壽,須歸,先調君勉、易一來辦事,急須開報。以用孔子紀年,及刊上諭事,江寧震動。適有京師劾案,遂藉此結束。”[40]康有為在1896年1月26日寫給何樹齡、徐勤的信中也提到過張之洞“排孔子紀年”的工作。[41]1897年康有為等人在桂林發起、組織的圣學會,也是以孔子紀元的。
既然康有為在戊戌變法之前就已經有了以孔子紀元的思惟和實踐,那么,給天子上一道建議以孔子紀元的奏折并非不成能之事,雖然事實并非這般。歷史學界往往以康有為重撰戊戌奏稿為有興趣作偽,這種評價疏忽了康有為重撰這些奏稿時能夠的心情。極有能夠的是,康有為重撰這些奏稿時不僅帶著良多遺憾,並且處于重演的設想之中。
是以,從某種意義上說,康有為重撰這些奏稿是對這些奏稿的重演性改寫。于是,不難懂得,在這些重撰的奏稿中,改寫的內容有的是他戊戌以后才有的思惟,有的則是他在戊戌時已經有但由于種種緣由當時未能寫進奏折的思惟。
值得留意的是,在年夜約寫于1902年的《致張克誠書》中,康有為提到戊戌時他曾將以孔子紀元的建議進奏:“仆不幸以身任國事,踐于患難,遂不克任此。而夙昔所著之書,發明孔子改制,以孔子紀年,并開儒教會,曾經進奏,微旨所存,未嘗一日忘之。”[42]
我們并不克不及由此推斷說國教折的撰寫不晚于《致張克誠書》。後面已經論及,《我史》中“光緒二十四年”條下“并進呈《孔子改制考》,請聽沿邊港口準用孔子紀年”之語的添加要早于國教折的撰寫。《致張克誠書》也能夠早于國教折的撰寫,因為康有為很早就“信任”本身曾經將以孔子紀元的建議進奏。其實,既然以孔子紀元是康有為很早就有的思惟,我們卻是可以由此推測,大要后來康有為一向遺憾本身沒有在戊戌期間將以孔子紀元這一條寫進建議設立儒教的奏折。
關于以孔子紀元的問題,一個更值得留意的處所是,在國教折衷,康有為并不是主張要將原有的紀元徹底廢棄不消,更換為以孔子紀元,而是建議將以孔子紀元與原有的紀元并行,其所舉的先例便是以開國紀元與時王年號并行的japan(日本)。在上引《年夜同書》論紀元問題時,康有為徵引japan(日本)的情況以提出宜以教主紀元和年夜同紀元并行。而同樣徵引japan(日本)的情況來說明中國宜以孔子紀元和清朝原有的紀元并行則不僅見于國教折,也見于《英國監布烈住年夜學華文總教習齋路士會見記》和《歐美學校圖記 英惡士弗年夜學校圖記》:“宜以孔子紀年,以統中國數千年之記事,用省煩瀆,而與國朝今之紀元并行,如japan(日本)之以明治君號紀元,而又以神武天皇紀元二千五百年同為并行焉。”[43]
回到國教折的內容。在說明以孔子紀元的來由之后,康有為將本身的一攬子建議作了總括性的說明:
“伏惟皇上圣明,傳心先圣,敬教審時,洞達中外,乞明詔設立教部,令行省設立教會、講生,令平易近間有廟,皆專祀孔子以配天,并行孔子紀年以崇國教。其祀典舊多誣濫,某人稱雜糅,魔鬼邪奇,或無好事,應令禮官,考據經典,嚴議裁汰。除各教風行久遠,聽平易近信教不受拘束,及祀典昭垂者外,一切淫祠,乞命地點有司,立行罷廢,皆以改充孔廟,或作學校,以省妄費而正教俗。”[44]
這里既主張立國教、又主張崇奉不受拘束的思惟亦見諸《英國監布烈住年夜學華文總教習齋路士會見記》和《歐美學校圖記 英惡士弗年夜學校圖記》:
“蓋他教雖各有神圣,而中國數千年風俗之宜、好事之盛,無有如孔子者,此為吾國國教也。平易近間鄉曲,宜盡廢淫祠而遍祀之,立諸生以同講勸焉,一如歐佳麗之祠耶穌,立祭司、牧師包養管道也。……宜立孔教為國教,而其余聽平易近之不受拘束崇奉,如歐人之以耶穌或上帝為國教,而以其余聽平易近之信仰不受拘束也。”[45]
我們說,在主張立儒教為國教的同時又主張崇奉不受拘束,這是國教折衷的一個主要思惟,而此中崇奉不受拘束的主張不見于保教折。國教折與保教折的這一差別,天然意味著康有為在分歧時期思惟的差別和立論角度的差別,而導致這一差別的還有一個更實際的原因,這就是康有為《請改直省書院為中學堂鄉邑淫祠為小學堂令小平易近六歲皆進學折》的實際后果。
這道奏折年夜約在光緒二十四年蒲月十九日(1898年7月7日)由軍機年夜臣廖壽恒進呈于光緒天子,之后很快就獲得了光緒天子的響應。茅海建經過查閱,得知軍機處《洋務檔》光緒二十四年蒲月二十二日錄有光緒天子朱筆修正過的明發上諭,此中的內容“完整來自”《請改直省書院為中學堂鄉邑淫祠為小學堂令小平易近六歲皆進學折》。茅海建還指出,“這是康有為奏議第三次被直接采用”。[46]關于光緒天子對這道上諭的重視,茅海建指出:“此后,光緒天子對此道諭旨的執行情況非常關注,并對各地的落實與進展非常不滿,七月初三日、初旬日還有兩道諭旨令各省敏捷將辦理情況上報。”[47]
在光緒天子的這道上諭中,關于改平易近間淫祠為學堂,是這么說的:“至如平易近間祠廟,其有不在祀典者,即著由處所官曉諭居平易近,一概改為學堂,以節糜費而隆教導。”[48]關于這段改淫祠為學堂的諭旨所導致的實際后果,茅海建說:“此段諭旨引發此后全國性改廟為學的風潮,各類廟產被奪事務層出不窮,許多有名的廟宇被訛詐。這也成了康有為后來的罪名之一。”[49]
事實的確這般。“廟產興學”的政策在各地的確導致了良多廟產被奪事務,從而也成了康有為后來的罪名之一。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中將改淫祠為學堂的舉措所引發的問題作為后來政變發生的緣由之一:
“中國之淫祠,向來最盛;虛糜錢幣,供養敗類,最為國家之蠹。皇上于蒲月間下詔書,將全國淫祠悉改為學堂。于是奸僧惡巫,咸懷恣怨。北京及各省之年夜寺,其和尚最有鼎力,厚于貸賄,能通權貴,于是路況內監,行浸潤之譖于西后,謂皇上已從西教,此亦激變之一小緣由也。”[50]
論者已經指出,將廟產被奪事務歸咎于康有為,在很年夜水平上是不公正的。在康有為的奏折衷,只是說改淫祠為學堂,并沒有將佛、道等教的廟宇包含在內,並且,在光緒天子的上諭中,也明確指出所謂淫祠的范圍只限于“其有不在祀典者”。[51]
論者認為,廟產被奪事務實際上與張之洞的主張更有關聯。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初七(1898年7月25日),光緒天子諭令將張之洞所著的《勸學篇》頒發各省督撫、學政各一部,并在諭旨中稱其“持平通達”。而在《勸學篇》外篇第三中,張之洞談到興學堂的經費問題時說:
“府縣書院經費甚薄,房屋甚狹,小縣尤陋,甚者無之,豈足以養師生、購書器?曰:一縣可以善堂之地、賽會演戲之款改為之,一族可以祠堂之費改為之。然數亦無限,何如?日:可以佛道寺觀改為之。明天下寺觀何止數萬,都會百余區,年夜縣數十,小縣十余,皆有田產,其物業皆由布施而來,若改作學堂,則房屋、田產悉具,此亦權宜而簡易之策也。……年夜率每一縣之寺觀取十之七以改學堂。留十之三以處僧道;其改為學堂之田產,學堂用其七,僧道仍食其三。計其田產所值,奏明朝廷旌獎;僧道不愿獎者,移獎其親族以官職,這般則萬學可一朝而起也。”[52]
由此可見,張之洞關于興學堂的建議比康有為的要激進得多,康有為只是主張將不在國家祀典的淫祠改為學堂,而張之洞則明確主張將佛、道等教的寺、觀的非常之七改為學堂。[53]
于是,不難懂得,康有為后來會就此事為本身辯護。在《我史》“光緒二十四年”條下,康有為提到此事時說:
“時年夜學堂已定,吾乃上折請于各省開高級學堂、各府開中學、各縣開小學,撥各省善后款及各規費以充學費。并請廢全國淫祠,以其室宇充學舍,以其租進供學費。二十一日奉旨允行。于時各直省蒸蒸爭言開學矣。吾以鄉落各有淫祠,皆有租進,故欲改以充各鄉落學舍,意以梵剎不在淫祠之列。不料處所無賴,藉端擾挾,此則非當時料想所及矣。”[54]
根據茅海建的查對,此處一切文字皆見于手底稿,沒有后來的添加。這就是說,在japan(日本)亡命期間寫作《我史》時,康有為已經針對毀廟興學問題而為本身辯護了。不過,其時他的辯護只是就事論事,說明本身的主張只是改不在祀典的淫祠為學堂,并沒有將梵剎歸進淫祠之列。
在《英國監布烈住年夜學華文總教習齋路士會包養軟體見記》和《歐美學校圖記 英惡士弗年夜學校圖記》中,我們又一次看到康有為就此事為本身辯護。他從國人“得新則棄舊,故絕無古物之保存”的遺憾說起,引出“近者毀梵剎以興學”的問題,然后提到本身戊戌年間毀淫祠的建議,申說此建議并未針對“有教之庵寺”,并暗示“毀梵剎以興學”的責任也不在光緒天子:“吾戊戌之主毀淫祠,乃為無名之廟宇耳,非有教之庵寺也。即欲毀棄,而一教之年夜,安有不明下詔書,辨析而后往取之?坐使吏胥之奉行不善,乃至僧尼震驚,是豈煥發明詔之初心哉?”[55]
此處康有為所謂“近者毀梵剎以興學”,有著真實的歷史佈景。
1901年,義和團運動之后,慈禧太后主導朝政,奉行新政,史稱“清末新政”。新政的一項主要舉措就是興學育才。而在若何解決興辦學堂的經費問題上,新政的有關政策文件中的確有“可借公所寺觀等處為之”等廟產興學的內容。盡管這些政策文件對于廟產興學只是包養心得提了一個粗略的標的目的,此中并沒有具體的規定,但各地在督撫的支撐和官員的主導下,毀梵剎以興學的現象屢屢發生,直到1905年朝廷頒發保護寺廟產業的上諭。[56]
值得留意的是,在討論毀廟興學問題的這些文字之前,正是後面已經援用過的“宜立孔教為國教,而其余聽平易近之不受拘束崇奉”等文字。假如將前后的文字關聯起來,那么,我們可以看到,康有為在此處就毀廟興學問題而為本身所做的辯護就不像《我史》中那樣僅限于就事論事,他實際上是將這個問題上升到政管理念和軌制設定的高度,就是說,從政管理念和軌制設定而言,最能夠表白他沒有毀他教之思惟的,就是在主張立儒教為國教的同時也主張崇奉不受拘束。
上引國教折的最后一段專門提到其他宗教也是要申說立儒教為國教的同時也要倡導崇奉不受拘束:“除各教風行久遠,聽平易近信教不受拘束,及祀典昭垂者外,一切淫祠,乞命地點有司,立行罷廢,皆以改充孔廟,或作學校,以省妄費而正教俗。”這就是說,假如說康有為后來作國教折,有興趣就他改淫祠為學堂的建議所引發的毀廟興學問題而為本身辯護的話,那么,在此折衷他的辯護與他在《英國監布烈住年夜學華文總教習齋路士會見記》和《歐美學校圖記 英惡士弗年夜學校圖記》中的辯護是一樣的,二者都將這個問題上升到政管理念和軌制設定的高度上而倡導立儒教為國教和崇奉不受拘束并行不悖。[57]
別的,國教折衷“官立教部以統國教,其余皆聽平易近之不受拘束崇奉”的主張,亦見于《官制議》的第十一卷“增司集權”。改書第一版由上海廣智書局于1904年7月發行,此中多卷刊載于1902-1904年的《新平易近叢報》,但第十一卷“增司集權”并未在《新平易近叢報》刊載。在這一卷中,康有為倡導立教部以掌國教,其言曰:
“教部掌布宣國教之事。俄、土、波、英皆有教部,與當局對舉,最為主要。法、意、普則以教部兼法部,奧、匈、瑞、希則以文部兼教部。蓋各國之憲法,崇奉各教,雖聽人自立,而本國之政治、人心、風俗,則各有其國教之宜,不成掉墜也,故皆設教部以統之。中國政治、義理、學校、選舉皆出于儒,故禮部者實教部也。但禮部于供奉為多,亦兼領學校、風俗之事,職不專純,今宜正其名曰教部。各省學政,皆改為提督教事。各府各縣皆立教長,各鄉皆立掌教。教生即以今舉人、秀才之耆宿有德看誠心者充之,以教其鄉人。其一縣之教長,由各鄉掌教公舉,而提督教事定之;一道、府之教長,由各縣之教長公舉,而教部長主之;一省之提督教事,由各道、府之教長公舉,而教部長請旨任之;教部長由各省提督教事公舉,奏聞而簡任焉。自軍旅、獄室,皆置教生以教化之。其各縣、鄉淫祀,皆改為圣廟,立教生以司之。其有教案,皆由教部交涉。其行教于外國者,重賞而后禮之。”[58]
教部之名,已見于保教折,在那里是說所要立的儒教會“略如外國教部之例”,而“其于禮部,則如軍機處之與內閣,總署之于理藩院”,便是以儒教會統屬于禮部。而後面已經提到,在《教學通義》中,康有為倡議設立道學科,在治理上亦是統屬于禮部;在1898年6月21日進呈給天子的《japan(日本)變政考》中,康有為則建議“改禮部為教部”。
在國教折衷,康有為的表述則是“官立教部,而處所立教會”,還提到以全國教會之長為教部之最高官職,即教部尚書,沒有提到禮部。在《官制議》第二卷“中國古官制”論教官時,康有為一如他在《教學通義》中一樣,將敷教之官追溯至“契作司徒”,更提出中國設立教部是在四千年前:“契之司教,蓋在教部、文部之間,蓋文與教原附近。而中國之為教,并非如各國之托于神道,令人科學,但在人倫日用之間。各國以佛、回、耶蘇之法皆托于神,遂幾若身教必托于神,舍神言人若無教者,甚且以中國為無教,真不成解也。豈知中國之立教設部,乃在四千年前乎?”[59]
在《官制議》第十卷“存舊官”中談到禮部時,康有為說:“今新定百司,不存此部。”[60]于是我們看到在第十一卷“增司集權”中立教部的主張,而其言則曰“禮部者實教部也”,“今宜正其名曰教部”。由此可以看到,教部、教會之名,以及各級教會的教長之名,在各個文本中雖多有分歧,但前后意思并沒有實質性的差別。只是在保教折衷明言以衍圣公為儒教會之長,而在后來的文本中則沒有此議。《官制議》第十一卷“增司集權”中還有一些內容與保教折相同,好比談到東方教部與當局對舉、通過教部解決教案問題、獎賞在國外傳儒教者等。但就其焦點思惟而言則與國教折更為接近,即還是明確闡發立儒教為國教與崇奉不受拘束二者并行之義,且明確提到憲法問題。
在1917年7月19日的《致馮國璋電》中,康有為曾說:“仆戊戌以來掌管君主立憲,自辛亥以來掌管虛君共和,光亮言之,未有改也。”[61]康有為的君主立憲思惟雖然可以追溯到很早,好比約寫于1888年前的《實理公法全書》,而其首言立憲,則是在1897年的《上清帝第五書》中,可是,在戊戌變法期間,康有為并沒有專門就立憲問題向朝廷提出建議。[62]
康有為明確以君主立憲為其焦點的政治主張是在戊戌變法掉敗后的亡命生活中。[63]而國教折衷立儒教為國教與崇奉不受拘束的主張是與其君主立憲思惟完整分歧的。並且,從下面的陳述和剖析可以看到,國教折衷有多處內容和康有為后來一些文本中的內容雷同。這些內容計有:論神道教與人性教之別而以孔子為文明世之教主;斷當下的時代——包含東方——為據亂之世、尚未達至升平之世;駁孔子乃哲學家、政治家、教導家而非教主;說教主、君主紀元并行;倡立儒教為國教與崇奉不受拘束并行;辯戊戌廢淫祠之策不含佛道寺觀;說各國學校皆隸于教等。
與國教折的這些內容雷同的文本計有:《意年夜利游記》、《英國監布烈住年夜學華文總教習齋路士會見記》、《歐美學校圖記 英惡士弗年夜學校圖記》、《蘇格蘭噫巴顛年夜學參觀記》、《官制議》等。值得留意的是,這些文本年夜都寫作于1904年。所以,基于以上的剖析,我們可以斷言,國教折的寫就大要在1904年或稍后。[64]
既然國教折反應了康有為亡命期間的思惟,那么,可以說,國教折是偽而不廢。實際上,國教折最能代表康有為亡命期間的儒教思惟,他在亡命期間的其他處所談到儒教問題的,宗旨基礎上不出國教折,雖然還有一些新的內容值得重視。
關于儒教是不是宗教的迷惑,觸及對宗教概念的懂得,而康有為屢次為之申說。上引《意年夜利游記》中區分神道教與人性教的文字,就屬于康有為申說儒教為宗教的內容。在那一段文字之前,還有一段更具歸納綜合性的文字:“或有謂宗教必言神道,佛、耶、回皆言神,故得為宗教;孔子不言神道,不為宗教。此等論說尤奇愚。試問古人之識有‘教’之一字者,從何來?秦、漢以前,經、傳身教者,不成勝數。是豈亦佛、回、耶乎?信如此說,佛、回、耶未進中國前,然則中國數千年為無教之國耶?豈徒自貶,亦自誣甚矣!”[65]
而在《英國監布烈住年夜學華文總教習齋路士會見記》和《歐美學校圖記 英惡士弗年夜學校圖記》中,康有為的申說更為具體,重要包含如下三個要點。
起首,他指出,教的概念為中國所本有:
“試問教之為文義,并非日文,亦非西文,乃出于吾之古經傳記者也。若《書》之稱‘敬敷五教,在寬’、‘教胄子’,《易》言‘教思無窮’,《論語》言‘子有四教’,《孟子》言‘教亦多術’,又曰‘教以人倫’、‘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史記》稱‘仲尼門生以友教于四方’此皆至近之說,人人共知。教之為義至淺,亦人人共識,豈有數千年文明之中國而可無教?又可無掌管教化之人乎?若數千年之中國而可無教也,則中國人不皆淪為禽獸乎?”[66]
又說:
“夫教者,中國之名詞。教者效也,凡學、覺、交、效、爻、孝,皆從此義。年夜意乃以二物相合,先知覺后知,先覺覺后覺,一人先立道術,后人從其道而效之之云耳。中國既自有其教數千年,而《史記》秦扶蘇稱‘諸生皆效法孔子’,漢武帝稱‘諸子不在孔子之道者,絕勿進’,而學者束發讀經,進學皆拜孔子,包養管道言義皆調和于孔台灣包養網子,猶歐之奉耶,突厥、波斯之奉回。其中國數千年之實事,而非夢囈虛幻之言,雖愚者亦皆知之也。夫舉國數千年皆尊奉其道而效之,不謂之有教、不謂之教主而謂何?”[67]
其次,他指出japan(日本)人受釋教影響而將西文的“religio包養網評價n”翻譯為“宗教”,極為欠亨:
“日人之于華文訓詁,多所未愜。如‘不受拘束’、‘經濟’等詞句,皆與中國本義相反。即‘體操’二字,在中國文法,只可曰‘操體’乃通。而其行文又習于佛典之重文,若‘慈善’、‘英勇’、‘堅固’等字,必用雙名。由是主名百物,多用雙字。如教主立教之教,而必曰‘宗教’;教學之教,而必曰‘教導’。此古人迻述日文視為確然不刊者,實考之而皆極欠亨者也。夫‘宗’之與‘教’,二文本不相關,中國自古名詞,有言祖宗者,有言宗廟者,未有言宗教者。日人之為此名詞也,始出于佛學者也。自唐世佛學分離,于是《傳燈錄》分五宗,乃有禪宗、露臺宗、慈恩宗、華嚴宗之目,其后禪宗中又分宗,曰臨濟宗、溈山宗、仰山宗、云門宗、高眼宗、曹洞宗。所謂宗者,猶戰國諸子之分曰某子,后世漢、宋之爭曰某學,又曰某派、某門云耳。又如人家族姓,所謂繼嗣為宗,太史公所作《五宗世家》,古人所謂某房云耳。撰錄之僧,偶作名詞,本無意義,日人又增添本愿宗、真言宗、凈土宗、機密宗焉。日人以其復文之俗習讀傳燈之書,乃取‘宗’字加于‘教’上。蓋當時,教者系專指釋教言之,宗者專指釋教下諸宗派言之也。教大批小,以‘宗’加諸包養心得‘教’上,已年夜不適矣。”[68]
再次,他指出,對于西文“religion”一詞,應當廣義地輿解,即從內涵上看應當包含“一切諸教”,而不僅限于神道之教,就是說,西文的“religion”與中國本有的“教”的概念就其內涵而言“別無殊異”:
“本日人宗教之名,本由譯歐美之書而出。蓋因歐人向宗耶氏,別無他教,故其名謂之厘利盡Religion。厘利盡者,謂凡能樹立一義,能倡徒眾者之意。然則與中國所謂教別無殊異,所含廣年夜。或謂中含神道之義,則因耶教尊天主,而歐土之教只要耶氏,故附會之,并非厘利盡必限于神道也。若令厘利盡之義必限于神道,則當以神道譯之,而包養留言板不成以宗教稱之,又或以神教稱之,而不成以宗教稱之。本日人以佛氏宗教之詞譯耶氏厘利盡之義,耶少變佛而本出于佛,回少變耶而實出于耶,其同為神道,固皆一也。然若限于神道為教,則宇宙甚年夜,立教甚多,豈必盡言神道者?凡能樹一義,以招徒黨而傳于后者,茍非神道,則以何名之?以何譯之?既無其他名詞,則亦不克不及不以厘利盡目之。則厘利盡亦應為一切諸教之廣義,而不克不及僅為神道之專詞矣。”[69]
在康有為將儒教歸為宗教的同時,也時時強調儒教與佛、耶等神道之教之間的差異,此中的要點已見諸前引康有為區分神道教與人性教的文字。而在其它處所,康有為對儒教與佛、耶之間的差異也多有闡發。
在寫作于1901年的《中庸注》中,康有為在注“鬼神之為德”時援用《禮記》中所記載的孔子論鬼神的話來說明孔子神道設教之意,又以鬼神問題衡定佛、耶、孔三教:
“《記》曰:‘知氣在上’,‘魂氣無不之’,鬼也;‘是有精爽,至于神明’,神也。‘游魂為變’,鬼也;‘精氣為物’,神也。總而言之,凡兩間靈氣昭明充塞,雖在人性之外,而體乎物氣之中。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魂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黎則,百眾以畏,萬平易近以服。’孔子意也。佛氏專言鬼,耶氏專言神,孔子兼言鬼神,而盛稱其德。惟程朱以為六合之功用,張子以為二氣之良能,由于阮瞻《無鬼論》來,于是鬼神道息,非孔子神道設教意也。泰初多鬼,中古少神。人愈智,則鬼神愈少。固由教化,然其實終不成滅也。”[70]
後面還曾提到,康有為早年就有基督教出于釋教的觀點,在《意年夜利游記》中,他再次發揮此義:
“吾于二十五年前讀佛書與耶氏書,竊審耶教全出于佛。其言靈魂,言愛人,言異術,言懺悔,言贖罪,言地獄、地獄,直指本意天良,無一不與佛同。其言一神創造、三位一體、天主萬能,皆印度外道之一切。但耶改為末日審判,則魂積空虛,終無進地獄登地獄之一日,不如說輪回者之易聳動矣。其言養魂甚粗淺,在釋教中僅登斯陀含果,尚未到羅漢位置。”[71]
此處康有為還從印度、波斯、希臘、巴勒斯坦等地輿地位的關系及相關歷史說明印度九十六外道極有能夠很早就傳至猶太人地區,并列舉了二十個方面申說“以外儀觀之,耶教亦無一分歧于釋教焉”。[72]
不論基督教出于釋教的觀點在歷史發生學的意義上能否成立,從教化類型學的角度將基督教和釋教放在一路而與儒教區別開來,都是有事理的。康有為早年的陽教與陰教之別,或許我們在評論中提出的文教與宗教之別,的確是刻畫儒教或孔教與耶、佛等神道之教之差別的恰當方法。[73]
在論說基督教出于釋教而又比釋教淺易的同時,康有為還刻畫了基督教的兩個優點,即“切于愛人”與“勇于傳道”,指出這是基督教“雖淺易而年夜行”的最基礎緣由:“佛兼愛眾生,而耶氏以鳥獸為天之生以供人食,其道狹小,不如佛矣,改日必以此見攻。然其境詣雖淺,而奉行更廣年夜者,則以切于愛人而勇于傳道。”[74]
就“切于愛人”這一點,康有為指出基督教徒“不為深山寂寥閉坐絕人之行,日為濟人之事,強聒不已。包養金額” 就“勇于傳道”這一點,康有為指出“其傳道者曾以十三代投獅矣,耐勞苦、不畏逝世而行之。”[75]
不過,康有為又指出,雖然基督教“補益于人心不鮮”,但并不適合于中國,因為中國已有儒教,且其教旨無不備,又有釋教作為補充,何況從歷史來看基督教的傳教往往與暴力相關,猶不成取:
“耶教以天為父,令人人有四海兄弟之愛心。此其于歐美及非亞之間,其補益于人心不鮮。但施之中國,則一切之說,皆我舊教之一切。儒教言天至詳,言遷善改過魂明無不備矣。又有釋教補之,平易近情不順,豈能強施?因救人而兵爭,至于殺人盈城野,未能救之而先害之,此則不成解者矣。”[76]
關于傳教的主要性,我們已經指出,康有為早在長興教學時期就很是重視了,在其教學綱領中已經有了“廣宣教惠”一條。在寫作于1907年的《西班牙游記》中,康有為舉孔子的言行再次鄭重申說傳教之于弘道的主要性: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教之年夜與否,不在其旨之高深,而在其傳之之法之得否。若今波羅特士頓教者,傳教之法最得者也。吾國教與回教旨以閉教為主,自保重其道,待人至誠,下問乃告之。夫全國不知其道,而敝帚自珍,安有至誠而來下問別人之教旨哉?此猶欲進而閉之門也,其難于自張其教矣。是故昔者孔子之徒七十,門生三千,徒六萬,侶行教于四方,則孔教遍中國矣。佛變婆羅門之法,僧徒行教于各國,則釋教遍于東亞。摩訶末以創行其教所至,以軍力破人之國,滅人之教,而自行其教。今所至印度諸佛跡,皆為回教所破滅,而易為回教矣。故非、亞二洲,熱帶之地,無在非摩訶末軍力所到,即無在非摩訶末教力所到。然其傳教待之軍力,不消軍力者則教不及,夫傳教不以托之于人人,此其教所以不廣也。惟今耶教之徒開窮僻之地,教愚野之人,無幽不僻,無遠不屆,無險不縋,到處開堂,地點說法,指天為教,令人易知,此其所以遍地球而年夜行也。豈無故哉?此亦傳教得掉之林也。有志于教者,亦可鑒矣。”[77]
別的,康有為還就儒教本身以及與中國的一些相關問題提出了他的見解和建議。如將中國人不知敬教歸諸儒教“敷教在寬”之特點,認為儒教的這個特點從歷史上來看有值得確定之處,但從現在及將來的實際境況而言,則亦有令人憂患之處:
“甚矣!吾國人之不知敬教也。彼敬教更甚,而教力之壓更甚,于是有千年之暗中世界。吾國敷教在寬,故不敬教,而教無壓力,故變化最速。……雖然,速變則速變矣,吾患其無自立之性也。各國于其本國言語、文字、歷史、風俗、教宗,皆最寶愛之,敬佩之,保留之,而后人道能自立,一國乃自立。故各國學堂、獄、醫必有其敬禮國教之室,不如是則殆比于野蠻人。況孔子之道,既兼含并包,又為吾國所產,尤為親切,與他國之尊他邦之圣者分歧,故應與阿剌伯之敬摩訶末同耳。”[78]
很明顯,這已經是在國平易近性的高度上衡定儒教之意義。
康有為還就儒教之經典與傳記提出一個建議。我們了解,康有為很早就標榜《禮運》和《儒行》。在1910年秋寫給梁啟超的信中,康有為說:
“《論語》、《孟子》、《年夜學》、《中庸》,本各自為書,合為四書,體實不類。今莫如以《儒行》、《年夜學》、《禮運》、《中庸》四篇合為四記,則精粗先后鉅細畢該。或五行,即《年夜戴》中《容經》,于禮容最精長期包養。《門生職》于意訓最善,抑合此為六,名為六記(其序則以《容經》在《儒行》后)。或以《門生職》附《孝經》同為小學,而此但為五記。”[79]
細察其意,似乎有將《論語》、《孝經》等列進小學而將新的四記或五記歸進年夜學之意。[80]對于以尊孔為宗旨的儒門信徒而言,此論可爭議處甚多。
關聯于康有為獨特的今文經學觀點所引發的宏大爭議及其客觀上所形成的經典位置的最基礎動搖等實際后果,我們說,今后要重建孔教,必須下一番功夫從頭衡定經典,這是今朝孔教重建的一項最為緊要的任務。[81]
注釋
[1] 孔祥吉:《康有為變法奏議研討》,遼寧教導出書社1988年版,第386頁。
[2] 見《康有為選集》第五集,第94頁。
[3] 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鑒注》,第442頁。
[4] 孔祥吉:《康有為變法奏議研討》,第350、386頁。《董子年齡學》即《年齡董氏學》。
[5] 有關康有為何故繕寫《孔子改制考》的具體剖析可參見孔祥吉:《康有為變法奏議研討》,第350頁以下。
[6] 見《康有為選集》第四集,第96頁。
[7] 見《康有為選集》第四集,第97頁。
[8] 見《康有為選集》第三集,第297-298頁。
[9] 見《康有為選集》第四集,第96頁。
[10] 參看上篇可知,這個見解正可溯源于《教學通義》。
[11] 見《康有為選集》第四集,第97頁。
[12] 見《康有為選集》第七集,第374-375頁。
[13] 見《康有為選集》第七集,第375頁。
[14] 見《康有為選集》第八集,第32-36頁。同樣的內容見諸亦系于1904年的《歐美學校圖記 英惡士弗年夜學校圖記》,見《康有為選集》第八集,第125-129頁。
[15] 參見陳熙遠:《“宗教”——個中國近代文明史上的關鍵詞》,載《新史學》2002年第12期,第53頁。別的。或許有需要指出,梁啟超1902年寫作的《保教之所以非尊孔論》一文,此中也是以“孔子為哲學家、政治家和教導家而非教主”立論。溯其淵源,這一觀點在japan(日本)學界比較風行,更早則來自基督教傳教士。
[16] 見《康有為選集》第四集,第96頁。
[17] 見《康有為選集》第四集,第97頁。
[18] 見《康有為選集》第四集短期包養,第97頁。
[19] 《年夜同書》手底稿“年夜同合國三世表”中談到升平世之宗教軌制時康有為說:“公商教義,兼采諸圣之長,以為新教。”此中“兼采諸圣之長”在1913年的《不忍》本和1935年的中華本中則作“尊天而兼采諸圣之長以配天”。見《康有為選集》第七集,第153頁。可見經過康有為后來修正的《年夜同書》才有了升平世之教當以諸圣配天的思惟。
[20] 陳煥章:《孔宅詩序》,載《宗圣學報》,總第十六號。
[21] 劉海粟:《憶康有為師長教師》,見《追憶康有為》,第309頁。
[22] 誠然,不成否認的是,康有為人人祀孔、人人祀天的儒教改造主張,的確遭到基督教的影響。在寫作于1914年12月的《國民祭天及圣袝配以祖先說》一文中,康有為認為人人祀天、祀孔、祀祖對儒教來說堪稱完備之禮,也明言此中人人祀天之義得自基督教的啟發:“故吾國平易近于地點地祀天及圣,以其神及祖先配之可也,義之至也,禮之隆也。基督教人祀天圣而不祀先,吾國平易近祀先而不祀天,其士祀圣亦不祀天,各出缺典,皆不完不備之禮也。孔子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蓋人性莫年夜于仁,而孝弟為仁之本。故祀天以明萬物皆本于天也,則萬物一體矣,所以教仁莫年夜焉;祀先以明身體與宗族皆本于祖、父也,則以親九族矣,所以教孝莫深焉。令國平易近皆仁且孝,人性備矣,全國治矣,孔子之道行矣。故及今宜令國平易近祀天及圣,以祖先袝配之禮。”見《康有為選集》第十集,第202頁。
[23] 見《康有為選集》第四集,第98頁。
[24] 錢穆1944年作《讀康南海》,此中說:“南海早年,實為歐洲文明之謳歌崇敬者,其轉而為批評鄙薄,則實由其親游歐土始。”見《中國學術思惟史論叢》,第八卷,325頁。
[25] 見《康有為選集》第七集,第374頁。
[26] 見《康有為選集》第四集,第98頁。
[27] 從現有文獻來看,康有為最早論及治教分途是在刊定于19世紀90年月初的《實理公法全書》的“教事門”條下:“治教本有天然分為二事之形,蓋一人不克不及同時兼任二事,且事體分歧,則人道多各有所長。”此為教事門中實理之二。其公法則曰:“教與治,其權各不相涉。”后加按語曰:“此乃幾何正義所出之法,最無益于人性者。”其比例之一曰:“行教者可侵政權。”后加按語曰:“此必無害。如某教士侵某國政權,則其害何如,皆可具征。”比例之二曰:“教事以行政者主之,教士包養網比較應得之權,行政之人,得以無幻想制。”后加按語曰:“這般亦無害。”見《康有為選集》第一集,第156頁。
[28] 見《康有為選集》第八集,第32頁。同樣的內容見諸《歐美學校圖記 英惡士弗年夜學校圖記》,見《康有為選集》包養網推薦第八集,第125頁。
[29] 干春松在《宗教、國家與國民宗教——平易近族國家建構過程中的儒教設想與儒教會實踐》一文中留意到康有為國教概念的特別之處,即康有為重要是從文明和風俗的角度來懂得國教的,該文見《哲學剖析》,2012年第2期,第4-34頁。
[30] 見《康有為選集》第八集,第32頁。同樣的內容見諸《歐美學校圖記 英惡士弗年夜學校圖記》,見《康有為選集》第八集,第125頁。
[31] 見《康有為選集》第八集,第55頁。
[32] 見《康有為選集》第四集,第98頁。
[33] 見《康有為選集》第一集,第154頁。
[34] 見《康有為選集》第七集,第142頁。
[35] 見《康有為選集》第七集,第143頁。
[36] 見《康有為選集》第七集,第143頁。
[37] 見《康有為選集》第七集,第144頁。“于今兩元并紀”《不忍》本、中華本作“以教主與年夜同并紀元”,故知此處的兩元并紀是指教主紀元與年夜同紀元并用。
[38] 見《康有為選集》第七集,第144頁。
[39] 見《康有為選集》第七集,第142頁。
[40] 見《康有為選集》第五集,第87頁。
[41] 見《康有為選集》第二集,第100頁。
[42] 見《康有為選集》第六集,第373頁。
[43] 見《康有為選集》第八集,第36頁,或第129頁。
[44] 見《康有為選集》第四集,第98頁。
[45] 見《康有為選集》第八集,第36頁,或第128-129頁。
[46] 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鑒注》,第495頁。
[47] 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鑒注》,第495頁。
[48] 引自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鑒注》,第494頁。此處茅海建還指出,上諭中“即著”原為“無妨”,“曉諭居平易近,一概”原為“酌量”,兩處皆由光緒天子朱筆改成,使其語氣減輕不少。不過,總的來說,光緒天子的這道上諭長短常平實的,甚至與康有為的奏折比擬也是這般。整個上諭中沒有出現“淫祠”的說法,只是說“其有不在祀典者”,並且,在康有為的奏折里,還有令禮官“考據經典,嚴議裁汰”以整頓“舊多誣濫”之祀典的建議,在光緒天子的上諭里則沒有這一條。
[49] 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鑒注》,第496頁。
[50] 見《飲冰室合集》第六冊,《飲冰室專集》之一,第72頁。
[51] 徐躍:《清末廟產興學政策的緣起和演變》,載《社會科學研討》2007年第4期。
[52] 轉引自徐躍:《清末廟產興學政策的緣起和演變》,載《社會包養網車馬費科學研討》2007年第4期。
[53] 張之洞就此提出的一個來由也很值得玩味:“方今西教日熾,二氏日微,其勢不克不及久存。釋教已際末法中半之運,道家亦有其鬼不神之憂,若得儒風振起。中華乂安,則二氏固亦蒙其保護矣。”這里至多有兩層意思值得留意:一是保中華方能保釋教、保道教,二是保孔教方能保釋教、保道教,而其所針對的皆是基督教在中國的興起,即所謂“西教日熾”的境況。
[54] 見《康有為選集》第五集,第95頁。
[55] 見《康有為選集》第八集,第37頁,或第130頁。就此事而為光緒天子明確進行辯護見諸《戊戌奏稿》麥仲華在國教折下的注:“按:淫祀與教導有異,然送上諭后,有司奉行不善,寺觀多毀。此胥吏訛索所致,非上諭意也。此折可證。仲華注。”轉引自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鑒注》,第496頁。茅海建認為此注是康有為以麥仲華的名義所寫。
[56] 參見徐躍:《清末廟產興學政策的緣起和演變》,載《社會科學研討》2007年第4期。
[57] 茅海建就上引“除各教風行久遠”這一段話評論說:“根據這一段話,即變成康建議可以保存風行久遠的佛、道及祀典所錄的各種寺廟觀院。康事后補作此論,以為本身洗刷。”見《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鑒注》,第496頁。這個評論很是不難讓人誤解為,康有為底本是主張毀各種寺廟觀院以興學,后來又反其初論而為本身開脫。
[58] 見《康有為選集》第七集,第311頁。
[59] 見《康有為選集》第七集,第236頁。
[60] 見《康有為選集》第七集,第296頁。
[61] 見《康有為選集》第十集,第418頁。
[62] 《戊戌奏稿》中有《請定立憲開國會折》、《請君平易近合治滿漢不分折》和《謝賞編書銀兩乞預定開國會期并先選才議政許平易近上書折》,根據黃彰健等人的研討,皆為康有為后來所撰,對此,茅海建評論說:“《戊戌奏稿》一連三篇特別炮制的另作,年夜談開國會立憲法,以致于后人多有誤解,將戊戌變法定性為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制的改進主義運動。”見《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鑒注》,第698頁。
[63] 1899年7月20日,康有為在加拿年夜溫哥華成立保皇會,繼續宣揚其君主立憲主張,是一個最明顯的標志性事務。
[64] 孔sd包養祥吉說國教折是康有為“到japan(日本)后從頭撰寫”,茅海建則猜測“其寫作時間很包養網ppt能夠在宣統年間”,皆無根據。分別見孔祥吉:《康有為變法奏議研討》,第385頁;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鑒注》,第496頁。別的,後面已說起,在寫作于1910年9月30日的《論中國宜用孔子紀年》中,康有為說:“昔在戊戌之歲,吾立儒教會于京師,士年夜夫多從焉。于是奏請令各省、府、縣、鄉皆立會,公舉耆舊志士學人為會長,改教官為奉祀官,諸生為講生,而京師立教部,令各省公舉教部長以總持焉,而于年夜事以孔子生紀年。事未行而新政敗,吾亦逋亡在外,十二年于茲矣。”見《康有為選集》第九集,第163頁。細察此語當對應于國教折:此中未提以衍圣公為儒教會總理而是說“公舉耆舊志士學人為會長”,此與國教折同而與保教折異;此中明確說到“于年夜事以孔子紀年”,此與國教折同而與保教折異;且《論中國宜用孔子紀年》一文中還有“康熙時學使吳培禁平易近婦祀孔子”的陳述,此內容亦見于國教折。故可斷言,國教折的寫就最遲在寫作此文之前。不過,既然國教折的內容與系于1904年的其他文本有那么多的雷同之處,我們大要可以斷言國教折的寫作即便不在1904年,也不會太晚。
[65] 見《康有為選集》第七集,第374頁。
[66] 見《康有為選集》第八集,第33頁或第126頁。
[67] 見《康有為選集》第八集,第34頁或第126頁。
[68] 見《康有為選集》第八集,第34頁或第126頁。在1923年的《長安講演錄》中,康有為大要出于“約定俗成”的考慮接收了日譯“宗教”一詞,而從“孔子講魂而運于人性之內”的角度闡述儒教相對于其他宗教的特點,前后觀點年夜同小異,見《康有為選集》第十一集,第275-276頁。
[69] 見《康有為選集》第八集,第34頁或第126-127頁。
[70] 見《康有為選集》第五集,第376頁。
[71] 見《康有為選集》第七集,第397頁。
[72] 見《康有為選集》第七集,第397頁。
[73] 尼采有弱者宗教與強者宗教的區分,對應于奴隸品德與主人性德的區分,與此處陽教與陰教的區分或文教與宗教的區分類似而又有分歧。
[74] 見《康有為選集》第七集,第398頁。
[75] 見《康有為選集》第七集,第398頁。
[76] 見《康有為選集》第七集,第398頁。
[77] 見《康有為選集》第八集,第291頁。
[78] 《意年夜利游記》,見《康有為選集》第374頁。
[79] 見《康有為選集》第九集,第166頁。
[80] 其以《論語》為曾子、子夏之學,有守約隘道之弊,見前;其論《儒行》比《孝經》深博,而《孝經》仍不成廢則又關聯于耶、孔之別:“然《儒行》比《孝經》實為深博,其名義顯切,或可代《孝經》也。然《孝經》所以鄭重者,實以父子之義為孔子所特重,故郊廟并舉,以祖配天。其與耶教異者在此。故以孝與仁并重,而中國國民獨多,即因于此。本日如仍重父子乎,則《孝經》似不成廢。若趨年夜同矣,則與商耳。”見《康有為選集》第九集,第166頁。
[81] 陸寶千說:“尋儒教之終不因長素而昌,實由長素之不善紹述尼山圣學之故也。”此義值得儒門同志沉思。見陸寶千:《平易近國初年康有為之儒教運動》,載《中心研討院近代史研討所集刊》第八輯,1983年6月,第91頁。